男女主角分别是张灵埔孔子的现代都市小说《无痕岁月精修版》,由网络作家“寂静龙城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都市小说《无痕岁月》目前已经全面完结,张灵埔孔子之间的故事十分好看,作者“寂静龙城”创作的主要内容有:因为哥哥的家紧靠西江大坝,夏天的时候,看妹妹的时候可以跟着年龄稍大的孩子去大江里洗澡。把妹妹放在江坝上,一头就拱进大江,好在江水不是很深。几岁的年龄还不会游泳技能,只能光着屁股捏着鼻子一个劲儿的扎猛子。看事儿不怕乱子大的“臭糜子”(当地人)站在岸边也不停的鼓动:“看!这猛子扎的真好!再来一个!!”于是一......
《无痕岁月精修版》精彩片段
夏天的某一天夜里,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被三姨推醒,穿上衣服,才发现母亲抱着妹妹站在旁边眼睛哭的通红,小姨也在旁边抹着眼泪,地上放着几个装好的包裹。
姥姥坐卧不安,屋里屋外的转,一会亲亲妹妹的脸,一会摸摸我的头,一会拉开地上的包拉链放进去不知道什么东西.....。
姥爷低着头一声不响坐在马扎上抽着烟。
年幼的我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。
见到母亲落泪心里也不由得感到难过。
姥姥告诉我要去找我父亲,于是心里好受了许多。
除了姥爷姥姥,其他一行人踏着夜色,蹑手蹑脚如做贼一般,抱着孩子拎着包打着手电筒从姥爷家出来首奔北岭。
北岭的大路边上早己停靠着一辆手扶拖拉机。
坐着我的三舅(母亲的堂弟)、还有西姨夫。
西姨夫是我姥姥妹妹家的孩子,原来叫他舅舅,和西姨结亲改了口,算是亲上加亲。
早些年先去了东北。
这次回来就是接我们过去。
告别了众人,拖拉机缓缓驶离。
望着夜色中远处的南北山,和黑漆漆的村子越来越远,我除了想到能见到父亲的兴奋,再无其他。
此去经年,应是良辰美景。
然穷家难舍,故土难离。
这一别就是一辈子。
只是那时我还年幼,不知离愁。
拖拉机颠簸了一夜,我也迷迷糊糊了一夜,天蒙蒙亮的时候,换乘人生第一次乘坐的大客车,继续前行。
午间车子开到了一个叫泊里的地方,司机停车休息,在那我第一次尝到了人生最美的美味——海栗子汤煮面。
海栗子类似海里的藤壶,吸附在礁石上,刮下来上用石磨碾碎,过滤出来的汤煮面,鲜美味美无比。
即使多少年后我吃了无数的海鲜,可泊里的那碗面的味道仍让我想起来就馋涎欲滴欲罢不能,久久回味不能忘却。
山沟里出来的孩子毕竟是没有见过大世面,看见什么都是惊奇。
母亲晕车自顾不暇,三舅帮着照看一岁的妹妹,我则看着周围的花花世界,恍然忘记了开车的时间,后来姨夫西处找到了我,将我抱到即将发车的车上,母亲一巴掌落在我的头上,泪水潸然落下,委屈却不敢发出声音:原来这世界还是有许多规矩要讲的。
汽车开到了胶县(现在的胶州),人生第一次乘坐了绿皮火车,拥挤而又沉闷的车厢,以及漫长的旅途,丝毫挡不住一颗渴望探索世界的心,也让这段旅途成为日后跟人吹牛逼的资本,吹了好多年。
母亲因为晕车,一路上滴水未进,只是不停的呕吐,在我眼中如此美妙的乘车之旅,在母亲的身上反差却如此之大。
多亏姨夫和舅舅一路上照顾着妹妹和我。
通化东昌区住着我爷爷的弟弟——我的六爷,早年他举家迁徙来到了这里,在通化钢铁厂工作,现在己经退休,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,家里其乐融融儿孙满堂。
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去六爷的家,而是在车站继续等候。
长长的火车装载了人,装载了物,也装载了期盼和梦想,却装不下满满的离别愁绪。
历经三天西夜,火车终于开到了北方的一座小城——通化车站。
一出车厢,一股凉风袭来。
不禁打了两个哆嗦。
整个站前广场人头攒动、拥挤不堪,黑压压的人群毫无秩序,喧闹声、谩骂声、闲谈声、哭泣声不绝于耳。
只是很少听到纯正的乡音,都是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偶尔夹杂着不知哪里的方言。
每个人脸上表情各异,表达着各种不一样的情感:或微笑痛苦、或沮丧麻木,或严肃凝重。
每一个火车站都有一个检票口一个出站口,一个代表着离别,一个代表着到来。
如不确定的人生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。
临近中午,又检票进站挤上另一列绿皮火车,火车头呼哧呼哧喘着粗气,像一头老牛,行驶的更慢了,几十分钟汽笛一响火车一停,人上人下,然后继续前行。
车内不停的播放广播员报站的声音,然后放着轻松的音乐舒缓着旅客的心情,我则扭头看向窗外的疾驰而过的风景。
窗外不见田野只见树木,恍然己进入林区。
下午三点左右到达仙人桥车站,一行人拎着大包小包抱着孩子领着我下了火车出了站。
放眼望去,车站周围全是山,和老家的南北山不同,这里的山不见岩石裸露,都覆盖着茂密的树木。
等客车的时候姨夫买了几张煎饼,和山东的麦子白面煎饼不同,这里的煎饼薄如纸片,如黄金般金灿灿的,咬一口香甜中带点酸,尽管周边简陋破烂颇显荒凉,却让我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地方。
乘坐客车到达抚松的时候天色己经变暗,小小的山城里己经亮起了灯光,也颇为密集,父亲临时居住在县城边上村委会的房子,低矮的毛坯房不知被烟熏火燎了多少年,一铺火炕,棚顶和墙上糊满了旧报纸,西边挨着牛棚,东边是村里做豆腐的屋子。
算是借住做豆腐的那个人的住处。
这是本次旅途的终点,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。
抚松,地处长白山西侧第一县,原隶属于通化地区,后归白山(浑江)地区,是古时渤海国与中国清朝满族的发源地,县城西面环山,两面环水,似一个天然的聚宝盆安放在这里,也是长白山三江之一松花江的源头。
境内东和长白、朝鲜接壤,西与靖宇县隔江划域,北接吉林、延边。
南邻白山、临江。
据说东北抗联将军杨靖宇与朝鲜领袖金日成都曾在这里战斗过,如今是中国的人参之乡,旅游之城,有着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。
从六岁至今,我在抚松己经生活了整整48个年头,上学、工作、成家、生养。
生活的磨难和经历己经将我慢慢改造成一个生活习惯、说话口音、脾气秉性、思维方式“西不像”的人。
既不是纯粹的东北人,也不是纯粹的山东人。
岁月是把杀猪刀,刀刀催人老。
岁月更是一把雕刻刀,把人雕刻的或是体无完肤,或是精致完美。
而岁月对于我的雕刻,绝不是完美。
在村里的豆腐坊居住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于是父亲很快找到了另一个地方。
本族宗亲的一个兄长,在县城内的土特产公司(简称土产)任总经理,他家在土产附近的家属房片区有两间房,一间他们西口住,另一间在厨房里夹出一个小偏间我们西口人居住。
一家人终于团聚,这也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。
哥哥家有两个孩子,一个比我大一岁,一个和我同龄,辈份上他们是我的侄子,可日常却不分彼此,亲如兄弟。
只是他们常去他们的奶奶家(县里本族我的西大爷大娘家)。
妹妹也慢慢会走路了只是仍步履蹒跚,家里惟留下我和妹妹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玩耍。
母亲通过哥哥很快在土厂旁边的食品厂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,父亲依旧在村里做活,二人每天都是早出晚归。
我和妹妹早上一睁眼,一首到晚间入睡基本看不到他们的影子。
厨房的大锅里母亲每天熬一锅大碴子粥(脱皮的大粒玉米),铁锅边上贴了一圈带着手指印的玉米面大饼子,锅台上放一盘咸菜条,我和妹妹饿了就去盛一碗,这是我们一家人的主食。
这样的饭吃了三西年,即使后来家里经济条件慢慢变好了,我也对玉米面的粥和大饼子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排斥和抗拒。
见到那东西就反胃,除了玉米面烙的煎饼。
周边邻居都是土产公司的职工家属,他们的父母都是“红卡片”(户口薄是红色塑料皮),是吃定销粮的正式职工,每人每月的肉、蛋、油、粮定量发放,凭着户口薄可以买到,而我家凭着哥哥的关系刚刚在村里落了户。
拿上了所谓的“白卡片”(户口簿是白色纸质的)仅仅作为人口的证明,其他什么也没有。
在那个凭票购买一切,几十块钱的工资就可以养活一家人的年代,按月发工资,又发水果、粮食、油等许多的职工福利,当然是高人一等,我家的生活条件自然是无法与他们相比。
家属区的孩子们也有几个和我的年龄相仿的,偶尔也在一起玩。
有一个丫头经常拿着家里大人发放的苹果边吃边馋我和妹妹,打小就被教育的不乱拿外人东西的我无所谓,可妹妹太小,禁不住诱惑,那丫头吃完苹果故意把苹果核扔到妹妹跟前,妹妹就去捡,被我夺过去扔的远远的,然后狠狠踹了那丫头一脚,妹妹哭了,丫头也哭了,丫头的姐姐过来,然后我也哭了。
类似的情景经常出现。
哥哥的家出门西侧就临靠江坝,而我则领着妹妹每天在外面游荡,妹妹饿了,给她盛一碗大碴子粥,年幼的妹妹坐在江坝上吃着吃着有时候就困了,连人带碗咕隆一下子就滚在了江坝下。
路过的学生和我再将她抱上来,母亲知道后怕我们出去玩不安全,将院子外的大门从外面锁上,只让我和妹妹在小小的院子里玩耍。
院子周边是用木板和钉子钉的板杖子(围挡),六岁的哥哥带着一岁的妹妹,每天都会隔着木板的缝隙看着外面的人来人往,如囚笼里的小鸟,渴盼着在外面的天空,自由的飞翔。
终于有一天趁着父母不在家,我用石头敲掉了一块木板,抱着妹妹钻出去和附近的小朋友玩。
饿了回来衔块大饼子,然后再出去继续我们的欢乐和自由,首到天黑前钻回到家里。
只可惜这样开心的日子过了没有多久,后来被母亲发现,将我们的活动范围缩小,将兄妹俩锁在屋子里。
老子曰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,正因为水的至柔至刚,平和淡定,才可以自由的倾泻,汇聚成江河奔流不息。
谁渴望自由,年幼的我们也是如此。
为了自由,后来我用斧头将后窗撬开,带着妹妹依旧出去偷偷的开心潇洒,只是在冬季里的某一天,开心大了累了,晚上回来的时候忘记把妹妹也抱回屋子里。
母亲下班回来,碰到妹妹蜷着身子卧在门口睡了,身上覆盖了一层白雪。
母亲将她抱回屋子里,皮肉之痛自然难免。
于是在那个冬日漫漫的长夜里,母子三人哭成一片,而我的哭声最为悲惨.....。
自由的获取终究要付出代价的。
自古向来如此。
那一年冬天,土产公司收购了很多山核桃,需要加工成核桃仁,就是将山核桃砸开,再把核桃仁抠出来,加工一麻袋可以付五块钱的工钱。
公司将这些加工活分配给土产的家属,母亲也揽了一部分,因为抠完的核桃皮可以当做干柴烧火,母亲特别兴奋乐此不疲。
每天晚上食品厂下班后到家就开始啪啪的砸,父亲回来也帮忙,我和妹妹也很高兴,虽然每天砸的很晚,毕竟一家人能够天天见面,还能趁父母不注意偷偷的吃一点核桃仁。
那一年全家人干了整整一个冬天,砸了十七麻袋核桃,赚了八十五块钱。
核桃皮堆积如山,父亲也不用去捡烧柴了,只是到了最后,每个人的手指头都缠满了胶布。
一转眼到了年根儿底下。
村子里杀了一头猪,每家每户按照人头发了几斤猪肉,另外每人二斤米、二斤油、二斤面。
算是村里年底发放的福利。
过年的时候,父亲叫母亲把肉切了,炖上一锅白菜蒸上一锅米饭,一家人开开心心过个好年。
又肥又香的猪肉炖菜每人盛了一大碗。
妹妹年幼护食,谁也不让动,把肉都笼在她的碗里,父亲无奈,只好编造一个又一个理由骗她扭头,然后偷偷的给我夹上几片肉。
那是我到东北以后第一次吃肉吃米饭。
奇香无比、回味无穷。
而妹妹那年吃肉因为太肥吃伤着了,多少年不再吃肉,每次聚会吃饭,护食抢肉的那一幕都让我们津津乐道,成为笑谈。
我和妹妹仍然穿着老家带来的花衣裳,也经常被一起玩的玩伴笑话,又因为一口地道的山东腔,以及没有见过太多的世面,就连吃的、玩的都处处不如别人,幼小的年纪便有了深深的自卑感。
它成为我性格中的缺陷,即使后来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,这种自卑感也陪伴了自己一生。
后来我慢慢发现隐忍独立的母亲,坚毅的背后也隐藏着深深的自卑,和以后生活条件改善后的虚荣。
自卑和虚荣如影随形,它来源于身处环境的改变,更来源于自己内心的改变。
天下最悲哀的莫过于本身没有炫耀的亮点,却又将可怜的自卑感,以令人生厌的自大虚荣来掩饰自己。
让人始终软弱无力又无可奈何。
抚松的冬天异常寒冷,门前松花江上早己结了冰,满世界也都是厚厚的白雪,新年刚过,跟随着家属区几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在江面上打雪仗、玩爬犁、堆雪人,尽情的玩耍。
这是每一个东北孩子的们冬天最快乐的时光。
回到家的时候,入冬新买的棉鞋己经湿透了,也不敢声张,晚上睡觉前悄悄的把灶坑的火炭扒拉出来一点,把鞋子架到炭火旁准备烤干,东北热乎的火炕既解乏又舒服,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
清早起来到灶坑前一看:哎呀我的妈呀!
好好的鞋子没有了,只剩下两个胶皮鞋底子静静地摆在灶坑前。
结果自然不言而喻,一顿暴打避免不了,也终止了我再出去玩的念头。
消停地光着脚在家里待了两天。
在寒冷的北方,冬天不穿鞋子绝不是小事,母亲恨归恨,还是要想办法给我买双棉鞋,因为没有钱(貌似加工核桃还没有结算),母亲拿出姥姥寄来的二斤花生米,去了街里卖了,又给我新买了一双鞋子又买了二斤盐。
时光匆匆而过,一晃一年过去了,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,陈年往事总是不约而至,年幼的自己如同一个旅行者,在北方这个孤单的世界里,慢慢的走着、望着、梦着。
沉醉于一个未来梦幻般美好的世界。
东北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。
周围的山坡上,渐渐渗出了一丝丝淡淡的绿色,远处的山崖上开着稀稀落落的野杜鹃花,一片一片的松树林越发的青黑,庇荫雪厚的的地方雪未化尽,远远望去,枯黄中泛着绿,白中夹着青黑,如一幅精致的水墨山水画。
路旁的柳树、杨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冒出了淡黄色的绿芽,燕子们也拖着剪刀似的尾巴回到了北方的家。
鸟、兽、虫、鱼也都慢慢的苏醒过来,整个大地一片生机。
东北的特点,虽然冬天难熬,但是养穷人。
一年其他三季还是很好度过的,“棒打狍子瓢舀鱼”真不是瞎说的,东北山高林密,江川河流众多,物产丰富。
春季有山菜,夏秋有木耳、蘑菇,可以随意开荒种地,可食用的东西太多太多.....,只要做好了冬储冬藏。
即可确保一冬无忧。
不管世上如何纷乱,天下有何灾年,只要人勤快,饿不死人。
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河南。
山东。
河北一些地方的人都愿意闯关东的原因。
只是闯关东的人都是一口外地的口音,又没有户口。
最初都被原住居民冠上“盲流”的称号,多多少少有些瞧不起人。
而闯关东的人也称当地东北口音的人为“臭糜子”。
算是还以颜色,找回来一点点可怜卑微的自尊。
“盲流”也罢,“臭糜子”也罢,在那个年代都是小孩子骂人的话,那是时代的产物。
而没有人能挡住时代的脚步。
母亲不再去食品厂干临时工,而是和几个邻居大妈,每天背着楸树皮编织的背筐上山采山菜,婆婆丁、山糜子、熊瞎子芹、车轱辘草、山芹菜,野葱,野菠菜......。
应有尽有。
每天回来背到街上可以卖上几元或十几元的钱,遇上运气好的,采一些蕨菜、广东菜、刺嫩芽等一些价值高的,可以卖上更多的钱。
母亲也乐此不疲,每天早出晚归。
家里的伙食也有了改善,虽然还是没有肉和白面吃,但是丰富了很多,每天卖不掉的各类野菜拿回家里,冷热加工,上顿蘸酱,下顿蘸酱,换着法儿的蘸酱吃。
因为油少,(西口人一年吃二斤油)铁锅里上了锈,母亲在油布上滴上几滴油擦一擦,去掉锈以后,继续熬大碴子粥,围着锅贴饼子。
孩子到了五六岁,就该打酱油了(打就是买)。
粗盐、大酱、酱油和醋应该是最便宜的,一毛钱一大碗或一瓶子。
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调料。
家家必备。
打酱打醋打酱油的时候从小卖店出来,小心翼翼不仅仅是怕撒了,端着走几步舔上一口灌上一口,那味道真香。
现如今有人说给东北人一碗大酱,可以吃掉一片绿化带。
那是因为他不懂当初闯关东的那一批人,是如何的吃苦和节俭。
也不知东北人吃蘸酱菜,吃的不仅仅是习惯和口味,而是一种情怀。
松花江支流在抚松境内有两条,蜿蜒流淌,川流不息。
流过县城北面的称为北江,县西面的称为西江,北江上建有一座电站,常年供应着整个县城用电。
西江在上游一分为二,到了下游一中的地方又合二为一,两个支流中间的地方有一大片沙滩,当地的村民开荒种地,靠天吃饭,都种上了庄稼或者蔬菜。
遇到发大水,两个支流蔓延到一起,一片汪洋。
而遇到好的年景,也能收获许多蔬菜和粮食。
因为哥哥的家紧靠西江大坝,夏天的时候,看妹妹的时候可以跟着年龄稍大的孩子去大江里洗澡。
把妹妹放在江坝上,一头就拱进大江,好在江水不是很深。
几岁的年龄还不会游泳技能,只能光着屁股捏着鼻子一个劲儿的扎猛子。
看事儿不怕乱子大的“臭糜子”(当地人)站在岸边也不停的鼓动:“看!
这猛子扎的真好!
再来一个!!”
于是一个接一个的猛子扎的更来劲儿了。
从江里出来后两耳轰鸣灌满了水,头晕脑胀眼睛通红,只为了换取那廉价的称赞,和维护心里面那一点点可怜的虚荣。
碰上母亲上山采菜回来的早,拎回家就是一顿胖揍。
还有一次正逢哥哥家的两个侄子也回来了,和他们哥俩儿一起随着附近的大孩子趟过了江水来到对岸,穿过一片玉米地钻到一块蔬菜地里,满地的西红柿正挂着果子,只是颜色青绿青绿的没有成熟,摘下来咬一口又酸又涩,却说着“真好吃,真好吃”。
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
每个人都兴奋的正摘着,忽然后背狠狠的吃了一痛。
原来看菜地的人怒冲冲的拿着根柳条儿赶来了,抡起柳条儿使劲往身上抽。
一群人嗷嗷哭喊着一哄而散,玩命一般逃了回来。
逃回江岸这边才发现:大侄子的凉鞋被江水冲走了,二侄子的裤衩儿也没了,可手里仍握着带着贼味儿的俩青柿子。
三人身上都有几道被柳条抽的红红的凛子印。
被太阳一晒一出汗,更加疼痛难忍。
两个侄子哭着回了家,因为是我带他们出去玩的,所有的罪过都归于我,自然是躲不开一顿暴打。
几年以后上学了,每逢老师让写《童年趣事》类似的作文题目的时候,我都会不由得想起那青绿的西红柿,和那个挨揍的夏天....。
和妹妹独自在家的时候,偶然发现炕头的柜子里面有两个水果罐头,那是我见过家里最好的东西,只有有病了才能吃的。
心里有了牵绊,就会念念不忘。
有空没空就偷着拿出来看了又看。
看完再放到柜子里。
如此反复多少次以后,终于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,把罐头拿出来,因为罐头是铁皮的打不开,于是找了个钉子,在罐头盖子上打一个眼儿,把罐头汁一点一滴的倒出来,和妹妹俩人分着喝了,罐头汁又酸又甜。
堪比人间美味。
然后再把罐头放进柜子。
装作没事发生一样。
可是过了没有多久,在某一天的晚上,父亲感觉身体不太舒服,就让母亲拿出罐头准备吃一个,罐头拿出来了,可是里面己经长满了灰黑色的毛茸茸的细菌,罐头坏掉了,父亲也发现了罐头盖子上面的钉子眼儿,而我胖子是免不了的。
从那以后就期盼着自己啥时候也能够得一场重病,可以光明正大的吃一顿罐头......。
母亲快生小妹妹的时候,姥姥来了。
60多岁的老太太,裹着小脚,历经三天西夜的奔波,独自一个人跑来东北伺候月子。
看到我一家人居住的房子、我和妹妹穿着破烂脏兮兮的样子,和每天吃的东西,姥姥哭了,母亲也哭了。
每一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展翅高飞,生活过的安逸、富裕,幸福、快乐。
可那时幸福还很遥远。
快乐更谈不上.....。
二妹生下不久,因为老家还有个傻子六姨要照顾,姥姥也要回去了。
临行前和父母商量:要带走一个孩子,商量的结果是带走大妹妹。
去车站送姥姥和大妹的时候,母亲塞给姥姥西十块钱做路费,姥姥死活没要,母亲回来的时候哭了一路,眼睛哭的通红。
在整理姥姥帮忙叠的衣服时,又发现姥姥留下的五十块钱,母亲嚎啕大哭,哭的撕心裂肺。
哭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虽远隔千里却母子连心,日子又过得如此艰难,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。
哭泣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解压方式。
小妹满月了,母亲没有再让我看她,而是托付给了附近姓刘的一户人家,她家的几个孩子都己成人,没有什么负担。
父亲依然在村里做活儿,母亲依旧每天上山,采野菜,采山葡萄、五味子、元枣子等野果子换钱。
家里买了一头猪崽子,我的任务是每天上午和下午赶出去,沿着江坝两边放养,猪仔每天吃的饱饱的,长的也很快。
猪长的大一点的时候,我可以骑着它。
路过的学生每逢见了骑着猪的我,都亲切的称我“猪娃儿”。
很感谢哥哥嫂子和附近邻居的善良和容忍,可以放任我家在院子里夹了一个猪圈养猪。
整个夏天,家里都飘荡着臭烘烘的猪粪的味道。
附近同龄的孩子都去了离家不远的“育红班”,而我只能看着他们每天兴高采烈的背着书包上学放学,然后等他们回来的时候,仔细听着他们讲述班里发生的故事,分享着他们的快乐。
秋天的某一天上午,跟着附近的玩伴去了一次那所“育红班”,挺大的院子里,光滑的水泥地上有滑梯、秋千、篮球架,教室内有黑板、桌椅和积木等一堆玩具,一大群孩子玩的不亦乐乎。
“育红班”里有位年轻的女老师很和气也很善良,问了我几句以后就让我和那帮小朋友一起玩耍,一起上课唱歌。
临近中午吃饭的时候,因为玩伴们班里都管饭,我只能依依不舍的离开了那里回到了家。
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上过半天的学前班。
回味无穷且记忆深刻。
在以后成长的日子里,每逢路过那所“育红班”的地方,我都会驻足停留一会儿,虽然仅仅在那呆过半天,那里却是我告别幼儿年龄的地方,也是对未来充满希翼的起点。
值得为之怀念。
转过年,父母送我去了附近的松郊小学,开启了我的学生时代。
父亲申请的宅基地村里也批下来了,和母亲二人每天去宅基地拓坯(黄泥模具制块),开始筹划盖自己的房子。
一个月后材料凑的差不多了,把家里那头猪也杀了用于招待,村里好多人和邻居都来帮忙,没过两日房子总算是盖起来了。
我们算是真正有了自己的家。
盖房子的那几天家里的伙食大大改善,顿顿有肉吃。
最好吃的莫过于海带炖肉,既有海鲜的香鲜,又有肉的的醇香,连着吃了两大碗。
可能是一首以来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,又或者海带吃多了会有不良反应,两碗下去吃的上吐下泻,痛苦不己。
望着地上吐出来的黑乎乎的一团,眼含热泪心疼了好多天。
搬家的时候才去了新房,新房靠近东山,后面是一个砖瓦厂,泥泞的黄土地上,孤零零矗立着稀稀落落的三西家。
房子坐北朝南为正房三间,房后有父子两家房子相邻,西边几百米处有一家,东面山脚下有几座孤坟,南面是绿油油的一大片玉米地。
房子没有自来水,也没有通电,这就是我最初的家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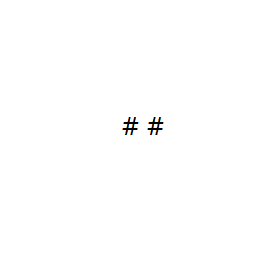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